作者:陳達
多少次午夜夢回,總是那一縷似曾相識的槐花香,伴著風鈴幽幽的節奏飄過半掩的窗,輕輕縈繞在記憶的邊緣。恍惚中宛若昨日重現,起身望去,斜掛在窗欞的卻已不是照在童年里的那輪月了。突然間,悵然若失,年華從眼前汩汩流過……
門前那棵大槐樹是什么時候種下的,就連娘也說不清楚。此刻回首,能想起的便是它年復一年的花開花落。在童年的記憶里,每當微微的綠意在枝頭悄悄萌發,我便得到大人的允諾,脫去厚厚的棉衣,像剛從冬眠中醒來的小松鼠一樣,在院子里撒開了歡兒。陽光從葉間的縫隙中透過,灑下一地斑駁的影子,沉寂了一冬的世界頓時變得靈動起來。陽光一天天暖了,大槐樹也開始羞澀地在春天里嫵媚起來。幾陣春雨過后,抬眼已是滿樹花開,這樣的盛情讓人措手不及,卻也異常驚喜。
小時候我出奇的頑皮,常常在黃昏的暮靄中脫掉鞋子爬到樹上,坐在樹杈間,悠然地晃著雙腿,隨手摘幾朵花放在嘴里嚼著。看著樹下小伙伴們羨慕的眼光,心里得意極了。那是我最引以為豪的時刻,因為我能看到更遠的地方。他們仰著頭問遠方有什么,我總是裝模作樣地遙望一番,然后很認真地說:“那兒有好大一個湖,湖邊是漂亮的房子,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住在里面。”他們半信半疑,只是始終沒人有勇氣爬上來。其實,我能看到的除了麥田還是麥田,只是隨季節變換改變著不同的顏色罷了,嫩綠,深綠,一直到金黃。很多年后,讀到海子的那句詩“遠方除了遙遠其實一無所有”,便有一片無垠的麥田從記憶里掠過……

那時候,每到槐花盛開的時候,也是人們心花盛開的時候,那個時候,吃的食物欠缺,村里的男女老少會用筐子弄來好多槐花。將一些洋槐花淘洗干凈,拌上適當面粉,碼在篳子上入鍋蒸來。洋槐花的香味透過鍋蓋氤氳沁鼻,唯有口水伴隨著我急切的心。待洋槐花蒸熟,用調好的蒜汁澆上,一道可飯可菜的“蒸菜”即大功告成。我迫不及待總是第一個把盛入碗中的蒸菜搶到手里,大快朵頤,連聲“好吃好吃好吃”。至洋槐花開敗,蒸菜可以吃上幾天。有的人家還會把一時吃不完的洋槐花曬干儲存起來,作為日后改善生活的食物。
我還清楚地記得,每年過年的時候,娘總要讓我站在大槐樹下,比著我的頭頂,在樹上刻下一道“身高線”。她撫著我的頭說:“希望我兒像大槐樹一樣快快長高,快快長大。”
那時候我會傻傻地想,長大,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吧。
后來,為了生計我四海為家。在汽車揚起的煙塵中,告別了故鄉,告別了大槐樹,告別了孩提時代的純真與夢幻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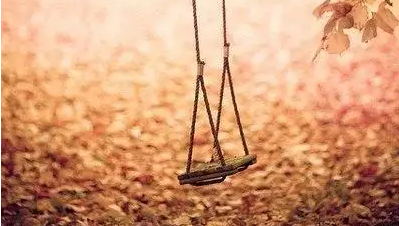
秋千架上隨風飄蕩的笑聲,站在槐樹下的少年,全部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情思,也在歲月里漸漸遠去……
歲月在不經意間慢慢積累,就這樣倉促地長大了,像坐在飛馳的列車上,窗外的風景迅速地向后退去,一閃而過,無法挽留,甚至來不及欣賞。只是在某一個被觸動的瞬間,記憶被一一翻閱的時候,才會知道,我來過,走過。那些曾經平凡而幸福的場景,我真真切切地擁有過。時空變換,歲月流轉,人生的公式在一步步的成長中不斷地被刪改,增添,直至重新定義。而有一些人、一些事卻在心里的一個角落珍藏著,不忍碰觸。它們糾結在生命的間隙,繞成一根不老的藤。滾滾的車流中,霓虹閃爍的夜幕下,總有一個輕輕的呼喚在心里低回不已。我知道,那是一片花開的聲音。
去年槐花飄香的季節,回應著那個久久不息的召喚,帶著赴約般的心情,我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老家。小村變化很大,原來的土房子已經不見了,所幸大槐樹還在。多年不見,它依然粗壯,高大,枝繁葉茂。夢幻般地,我站在樹下,虔誠地,一遍遍撫摩那十道疏密不等的刻痕,一遍遍回味那久已埋下的夢想……

那些年,我不斷地走進和離開,而且越走越遠,從小縣城,到小城市,最終將大都市的繁華盡收眼底。而它始終在這里佇立著,守候著我的回憶,櫛風沐雨,不離不棄。別后的歲月,它無法體會我所走過的傷痛與歡愉,正如我不能感受它所經歷的寒風與煦日。我們就這樣,在各自的世界中走過四季。輕輕地閉上眼,再一次俯在它挺拔的軀干上,說幾句悄悄話,用只有我們才能懂的語言。而它依舊靜默著聆聽,久久地不發一言。可我卻分明聽到了一聲顫抖著的嘆息,如此清晰,如此遙遠,仿佛是耳邊亦真亦幻的囈語,又像歲月長廊里漸行漸遠的足音……
如今,食不果腹對于小孩子們來說,仿佛天方夜譚,大多數人日益豐盛的碗里似乎淡出了迫不得已的,諸如用榆錢、構穗、槐花做的“蒸菜”,而這些口味我卻特別喜歡。我一直想在一個月光清冷的晚上爬上大槐樹,為它吹響一只短笛,在水樣的月色中等待下一次花開……
【作者簡介】陳達,男,筆名:田地。江蘇東海人。系臨沂市作家協會會員、連云港市作家協會會員,湖北省咸寧市作協《九頭鳥》雜志特邀撰稿人。現任《山花》雜志社執行主編。先后在《詩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鵑花》、《鴨綠江》、《青年文學家》《海風》、《參花》等報刊、雜志發表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報告文學等文章1000余篇。創作至今先后有文學作品被收入《文學連云港70年(散文卷)》、《臨沭古今詩詞精選》等三十多個版本的文集。并在全國性文學大賽中多次獲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