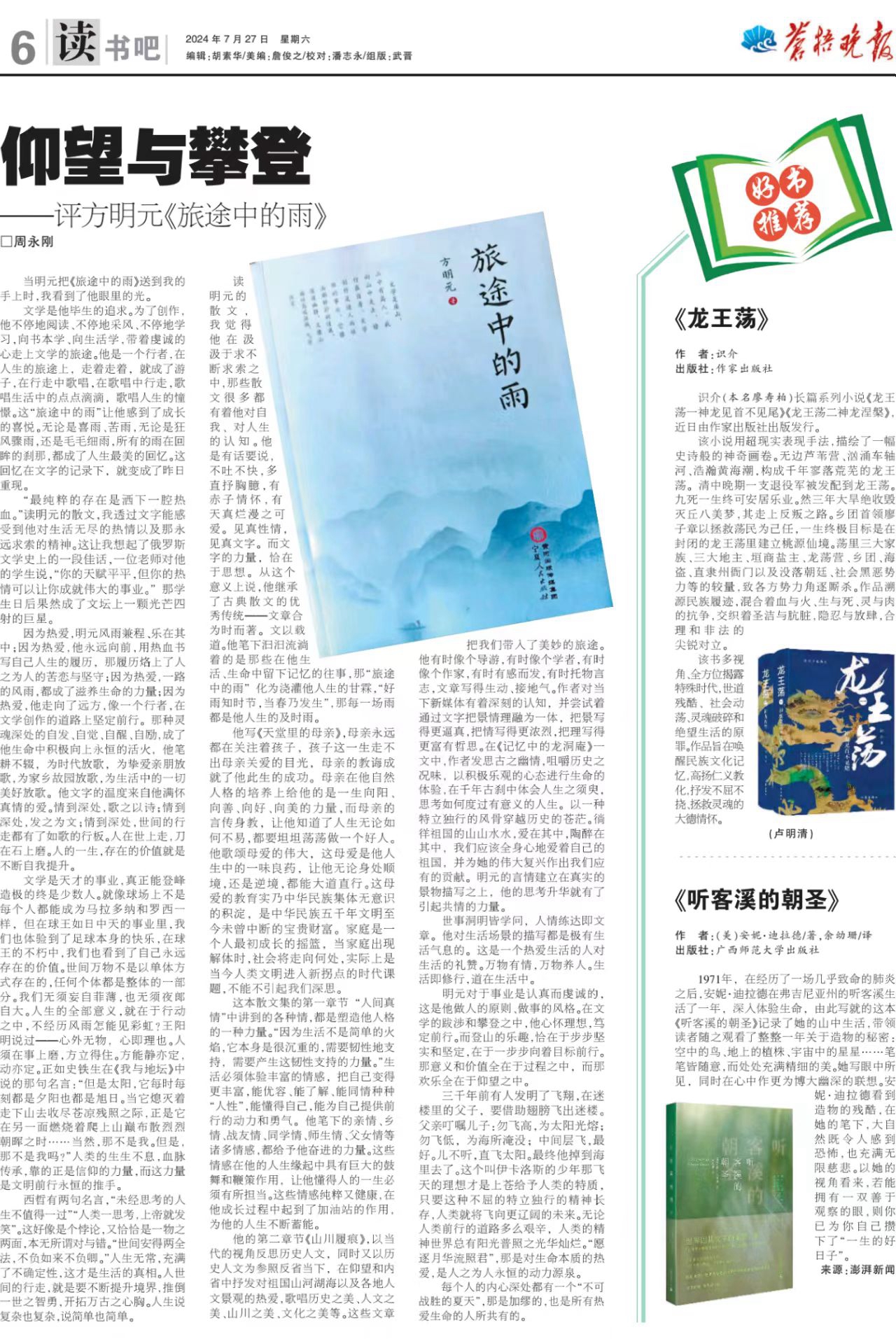 仰望與攀登
仰望與攀登
?———評(píng)方明元《旅途中的雨》
作者:周永剛
當(dāng)明元把《旅途中的雨》送到我的手上時(shí),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光。
文學(xué)是他畢生的追求。為了創(chuàng)作,他不停地閱讀、不停地采風(fēng)、不停地學(xué)習(xí),向書本學(xué)、向生活學(xué),帶著虔誠的心走上文學(xué)的旅途。他是一個(gè)行者,在人生的旅途上,走著走著,就成了游子,在行走中歌唱,在歌唱中行走,歌唱生活中的點(diǎn)點(diǎn)滴滴,歌唱人生的憧憬。這“旅途中的雨”讓他感到了成長的喜悅。無論是喜雨、苦雨,無論是狂風(fēng)驟雨,還是毛毛細(xì)雨,所有的雨在回眸的剎那,都成了人生最美的回憶。這回憶在文字的記錄下,就變成了昨日重現(xiàn)。
“最純粹的存在是灑下一腔熱血。”讀明元的散文,我透過文字能感受到他對(duì)生活無盡的熱情以及那永遠(yuǎn)求索的精神。這讓我想起了俄羅斯文學(xué)史上的一段佳話,一位老師對(duì)他的學(xué)生說,“你的天賦平平,但你的熱情可以讓你成就偉大的事業(yè)。”那學(xué)生日后果然成了文壇上一顆光芒四射的巨星。
因?yàn)闊釔郏髟L(fēng)雨兼程、樂在其中;因?yàn)闊釔郏肋h(yuǎn)向前,用熱血書寫自己人生的履歷,那履歷烙上了人之為人的苦戀與堅(jiān)守;因?yàn)闊釔郏宦返娘L(fēng)雨,都成了滋養(yǎng)生命的力量;因?yàn)闊釔郏呦蛄诉h(yuǎn)方,像一個(gè)行者,在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道路上堅(jiān)定前行。那種靈魂深處的自發(fā)、自覺、自醒、自勵(lì),成了他生命中積極向上永恒的活火,他筆耕不輟,為時(shí)代放歌,為摯愛親朋放歌,為家鄉(xiāng)故園放歌,為生活中的一切美好放歌。他文字的溫度來自他滿懷真情的愛。情到深處,歌之以詩;情到深處,發(fā)之為文;情到深處,世間的行走都有了如歌的行板。人在世上走,刀在石上磨。人的一生,存在的價(jià)值就是不斷自我提升。
文學(xué)是天才的事業(yè),真正能登峰造極的終是少數(shù)人。就像球場(chǎng)上不是每個(gè)人都能成為馬拉多納和羅西一樣,但在球王如日中天的事業(yè)里,我們也體驗(yàn)到了足球本身的快樂,在球王的不朽中,我們也看到了自己永遠(yuǎn)存在的價(jià)值。世間萬物不是以單體方式存在的,任何個(gè)體都是整體的一部分。我們無須妄自菲薄,也無須夜郞自大。人生的全部意義,就在于行動(dòng)之中,不經(jīng)歷風(fēng)雨怎能見彩虹?王陽明說過———心外無物,心即理也。人須在事上磨,方立得住。方能靜亦定,動(dòng)亦定。正如史鐵生在《我與地壇》中說的那句名言:“但是太陽,它每時(shí)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。當(dāng)它熄滅著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殘照之際,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燒著爬上山巔布散烈烈朝暉之時(shí)……當(dāng)然,那不是我。但是,那不是我嗎?”人類的生生不息,血脈傳承,靠的正是信仰的力量,而這力量是文明前行永恒的推手。
西哲有兩句名言,“未經(jīng)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過”“人類一思考,上帝就發(fā)笑”。這好像是個(gè)悖論,又恰恰是一物之兩面,本無所謂對(duì)與錯(cuò)。“世間安得兩全法,不負(fù)如來不負(fù)卿。”人生無常,充滿了不確定性,這才是生活的真相。人世間的行走,就是要不斷提升境界,推倒一世之智勇,開拓萬古之心胸。人生說復(fù)雜也復(fù)雜,說簡單也簡單。
讀明元的散文,我覺得他在汲汲于求不斷求索之中,那些散文很多都有著他對(duì)自我、對(duì)人生的認(rèn)知。他是有話要說,不吐不快,多直抒胸臆,有赤子情懷,有天真爛漫之可愛。見真性情,見真文字。而文字的力量,恰在于思想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說,他繼承了古典散文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———文章合為時(shí)而著。文以載道。他筆下汩汨流淌著的是那些在他生活、生命中留下記憶的往事,那“旅途中的雨”化為澆灌他人生的甘霖,“好雨知時(shí)節(jié),當(dāng)春乃發(fā)生”,那每一場(chǎng)雨都是他人生的及時(shí)雨。
他寫《天堂里的母親》,母親永遠(yuǎn)都在關(guān)注著孩子,孩子這一生走不出母親關(guān)愛的目光,母親的教誨成就了他此生的成功。母親在他自然人格的培養(yǎng)上給他的是一生向陽、向善、向好、向美的力量,而母親的言傳身教,讓他知道了人生無論如何不易,都要坦坦蕩蕩做一個(gè)好人。他歌頌?zāi)笎鄣膫ゴ螅@母愛是他人生中的一味良藥,讓他無論身處順境,還是逆境,都能大道直行。這母愛的教育實(shí)乃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(shí)的積淀,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至今未曾中斷的寶貴財(cái)富。家庭是一個(gè)人最初成長的搖籃,當(dāng)家庭出現(xiàn)解體時(shí),社會(huì)將走向何處,實(shí)際上是當(dāng)今人類文明進(jìn)入新拐點(diǎn)的時(shí)代課題,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。
這本散文集的第一章節(jié)“人間真情”中講到的各種情,都是塑造他人格的一種力量。“因?yàn)樯畈皇呛唵蔚幕鹧妫旧硎呛艹林氐模枰g性地支持,需要產(chǎn)生這韌性支持的力量。”生活必須體驗(yàn)豐富的情感,把自己變得更豐富,能優(yōu)容、能了解、能同情種種“人性”,能懂得自己,能為自己提供前行的動(dòng)力和勇氣。他筆下的親情、鄉(xiāng)情、戰(zhàn)友情、同學(xué)情、師生情、父女情等諸多情感,都給予他奮進(jìn)的力量。這些情感在他的人生緣起中具有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作用,讓他懂得人的一生必須有所擔(dān)當(dāng)。這些情感純粹又健康,在他成長過程中起到了加油站的作用,為他的人生不斷蓄能。
他的第二章節(jié)《山川履痕》,以當(dāng)代的視角反思?xì)v史人文,同時(shí)又以歷史人文為參照反省當(dāng)下,在仰望和內(nèi)省中抒發(fā)對(duì)祖國山河湖海以及各地人文景觀的熱愛,歌唱?dú)v史之美、人文之美、山川之美、文化之美等。這些文章把我們帶入了美妙的旅途。他有時(shí)像個(gè)導(dǎo)游,有時(shí)像個(gè)學(xué)者,有時(shí)像個(gè)作家,有時(shí)有感而發(fā),有時(shí)托物言志,文章寫得生動(dòng)、接地氣。作者對(duì)當(dāng)下新媒體有著深刻的認(rèn)知,并嘗試著通過文字把景情理融為一體,把景寫得更逼真,把情寫得更濃烈,把理寫得更富有哲思。在《記憶中的龍洞庵》一文中,作者發(fā)思古之幽情,咀嚼歷史之況味,以積極樂觀的心態(tài)進(jìn)行生命的體驗(yàn),在千年古剎中體會(huì)人生之須臾,思考如何度過有意義的人生。以一種特立獨(dú)行的風(fēng)骨穿越歷史的蒼茫。徜徉祖國的山山水水,愛在其中,陶醉在其中,我們應(yīng)該全身心地愛著自己的祖國,并為她的偉大復(fù)興作出我們應(yīng)有的貢獻(xiàn)。明元的言情建立在真實(shí)的景物描寫之上,他的思考升華就有了引起共情的力量。
世事洞明皆學(xué)問,人情練達(dá)即文章。他對(duì)生活場(chǎng)景的描寫都是極有生活氣息的。這是一個(gè)熱愛生活的人對(duì)生活的禮贊。萬物有情,萬物養(yǎng)人。生活即修行,道在生活中。
明元對(duì)于事業(yè)是認(rèn)真而虔誠的,這是他做人的原則、做事的風(fēng)格。在文學(xué)的跋涉和攀登之中,他心懷理想,篤定前行。而登山的樂趣,恰在于步步堅(jiān)實(shí)和堅(jiān)定,在于一步步向著目標(biāo)前行。那意義和價(jià)值全在于過程之中,而那歡樂全在于仰望之中。
三千年前有人發(fā)明了飛翔,在迷樓里的父子,要借助翅膀飛出迷樓。父親叮囑兒子:勿飛高,為太陽光熔;勿飛低,為海所淹沒;中間層飛,最好。兒不聽,直飛太陽。最終他掉到海里去了。這個(gè)叫伊卡洛斯的少年那飛天的理想才是上蒼給予人類的特質(zhì),只要這種不屈的特立獨(dú)行的精神長存,人類就將飛向更遼闊的未來。無論人類前行的道路多么艱辛,人類的精神世界總有陽光普照之光華燦爛。“愿逐月華流照君”,那是對(duì)生命本質(zhì)的熱愛,是人之為人永恒的動(dòng)力源泉。
每個(gè)人的內(nèi)心深處都有一個(gè)“不可戰(zhàn)勝的夏天”,那是加繆的,也是所有熱愛生命的人所共有的。
總值班: 吳弋 編輯: 朱蕓玫
來源: 連云港發(fā)布
